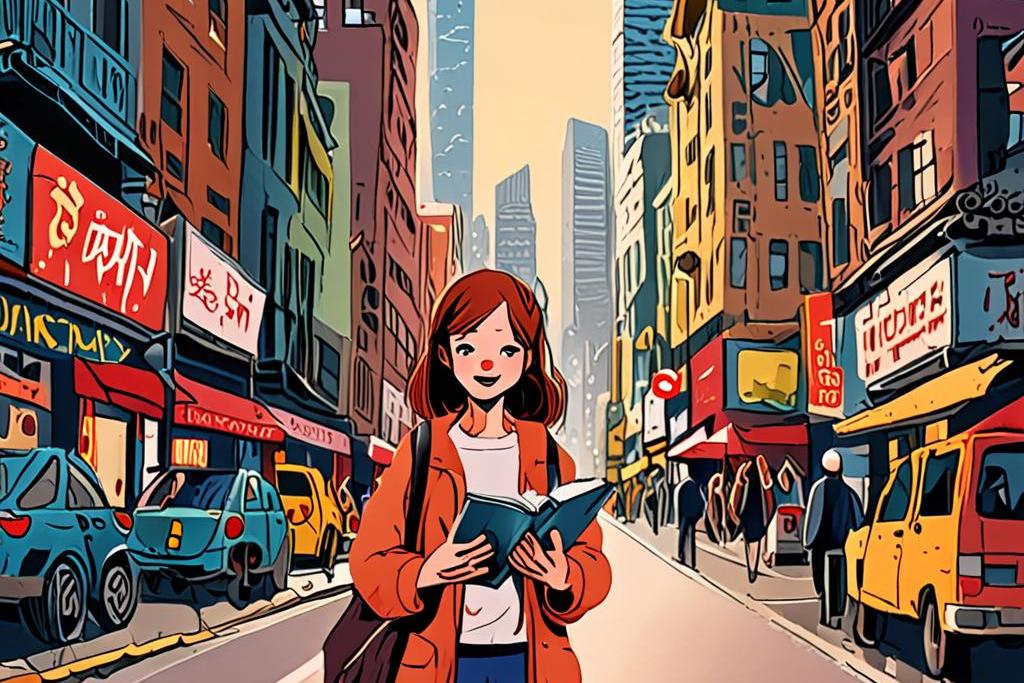为何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学区外学校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最近,奥克兰的麦克林斯学院(Macleans College)可谓是“火”出了圈,原因却让人大跌眼镜:该校在过去一年中一口气开除了九名学生,理由是他们在入学时存在欺诈行为。说白了,就是这些学生的家庭压根不住在麦克林斯学院的学区内,却为了蹭上这所名校的“光环”,不惜“狸猫换太子”,谎报地址,让自己看起来像模像样地住在学区内。中学校长协会主席沃恩·库尤伊特(Vaughan Couillault)在接受早餐节目采访时表示,这可不是什么“个例”,只要奥克兰的人口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就会“野火烧不尽”。
一位专家指出,入学欺诈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大行其道”了。人们之所以铤而走险,原因可谓是“五花八门”,但归根结底,还是逃不开“三座大山”:生活成本、住房危机和学区划分。
《新闻纵览》(Newsroom)采访了一位为了孩子上学而“剑走偏锋”的母亲,并请教了一位教育专家,试图揭开家长们向学校谎报地址的“难言之隐”。
为了孩子能接受稳定的教育,这位母亲选择“兵行险招”
为了保护孩子的隐私,我们暂且称这位母亲为索菲。30多岁的索菲是一位单亲妈妈,独自抚养着13岁的女儿,两人在奥克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据索菲回忆,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母女俩已经搬了11次家,租房、和家人同住,各种方式都尝试过,堪称现实版的“搬家达人”。索菲坦言,自己之所以一直居无定所,主要是因为生活成本高昂、住房市场“僧多粥少”,再加上和前伴侣分手以及“20多岁时的普遍不稳定”等一系列“幺蛾子”。尽管搬家搬到“怀疑人生”,但索菲硬是从女儿5岁起就一直让她在同一所学校上学,这波“神操作”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答案是:从一开始就“瞒天过海”,谎报地址。
原来,索菲的一位朋友住在索菲居住地附近一所学校的学区内,于是索菲就“借”用了朋友的地址给女儿报名。多年来,她一直把学校的邮件寄到朋友家,竟然也一直“相安无事”。索菲解释说,她和女儿住过的所有房子其实都和女儿的学校在同一个区域,但由于该区域人口稠密,学区被划分得非常“迷你”,这才导致了她们“看似近在咫尺,实则远在天涯”的尴尬处境。
“我们最后住的三栋房子都在同一条主干道上,开车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但都不在学区内,而且还分别属于不同学校的学区……仅仅因为它们位于主干道的哪一侧。” 索菲无奈地表示,“我可不想让她总跟着我‘打游击’,换来换去。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决定,绝不能让她总换学校。”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入学资格被取消,家长表示很“委屈”
教育部运营与融合负责人肖恩·泰迪(Sean Teddy)解释说,入学登记是在学生上学的第一天进行的,学生的地址必须在当时真实属于学区内,才有资格入学。
一旦成功入学,学生就有权留在该校继续接受教育,即使他们后来搬到了学区外的地址,学校也不能“过河拆桥”。不过,教育部也意识到,少数学校确实因为地址造假而出现了入学问题。泰迪表示:“如果提供的地址与实际情况不符,学校董事会有权在特定情况下取消学生的入学资格。” 他强调,如果一个家庭是因为在城市之间搬迁或住在紧急住房中而使用临时地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仅仅是为了进入一所学校而“挂羊头卖狗肉”,使用虚假地址,那就不符合规定了。
泰迪透露,截至2024年,已经有九名学生的入学资格被取消,其中八名来自奥克兰,一名来自尼尔森。他还表示,如果一个家庭对取消入学资格的决定提出上诉,教育部会进行审查,如果发现他们确实居住在学区内,可能会指示学校董事会重新录取该学生。
“蜗居”、学区房、教育资源……这位母亲的遭遇,道出了多少人的心酸?
对于索菲来说,找到一个适合孩子居住的经济适用房,简直比登天还难。她感慨道:“我们看过的房子,很多都惨不忍睹,比如那种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有一次,我们甚至去看了一栋没有窗户的房子!”
索菲表示,她之所以能租到现在的房子,完全是因为房东“佛系出租”,特别想把房子租给单亲妈妈。索菲的女儿明年就要上高中了,她表示会在女儿入学时提供真实的地址,因为她们现在住的地方终于“名正言顺”地属于学区内了。不过,她也坦言,如果在女儿上高中期间搬家,她会让女儿转学。“我不会在高中还像小学那样‘冒险’了……毕竟,高中是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对吧?他们确实需要这种稳定性。”
学区划分,真的是为了教育公平吗?
奥克兰理工大学教育学高级讲师斯图尔特·迪尔内斯(Stuart Dinnes)指出,赋予学校对学区划分的控制权,可能会加剧教育不平等。迪尔内斯解释说,学区划分制度最早是在1924年在小学实行的,1932年推广到中学,初衷是为了防止学校过度拥挤,并将学生均匀地分配到不同的学校。
他表示,二战后,新西兰人口激增,离校年龄提高到15岁,越来越多的学生希望接受更长时间的正规教育。正是在那时,学区划分有了一个更加“高大上”的目标:保护当地孩子在当地学校就读的权利,听起来是不是很“公平”?然而,到了1989年,“明日学校”计划横空出世,该计划鼓励学校实现更加自主的管理。“在此之前,政府在确定学区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但从那时起,我们看到了这种权力从中央集权控制到地方学校控制的转变。” 迪尔尼斯说道。这种变化导致一些更有实力的学校开始“暗箱操作”,将富裕的郊区纳入自己的学区,而将贫困的郊区拒之门外,以此来吸引更多“优质生源”。
他指出,如果一所学校看起来“高大上”,而且学生家庭普遍比较富裕,那么自然会有更多家长挤破头也想把孩子送进去。迪尔尼斯表示,一所学校的学生越多,获得的资金就越多,这将带来更多的教师和更多的机会,从而使学校看起来更具吸引力,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他认为,有些学生因为居住的地区有限,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另一些学生则“幸福”得多,他们有很多选择,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有很多学区重叠。他还表示,允许学校管理学区也可能是造成同一条街的不同街区属于不同学区的原因。
“可怜天下父母心”?家长“铤而走险”的背后,是无奈,还是“虚荣”?
对于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好”学校而“不择手段”的行为,迪尔内斯认为,这是被学校的“虚假”声誉所迷惑,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理性选择。“任何一所学校内部(在机会和成就方面)的差异都远大于学校之间的差异。所以,实际上,上令人向往的学校和不那么令人向往的学校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 他说道。
对于索菲的行为,迪尔内斯和索菲本人都认为算不上是真正的“欺诈”。迪尔内斯表示:“曾经发生过有人出租自己的邮箱,让他人用自己的邮箱地址……只是为了能够进入‘理想的’学校”,这与索菲的情况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认为,学校应该对学生家庭的实际情况表示同情和理解。“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故意撒谎以试图获得优势的人,那就不同于一个居无定所、走投无路的人。” 迪尔尼斯说道。他认为,学区制度需要一定的灵活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选择学校。
“这将创建一个有些人可以选择而另一些人无法选择的体系,这将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一些不平等现象。” 他总结道,“情况很复杂,我们需要一个更完善的体系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