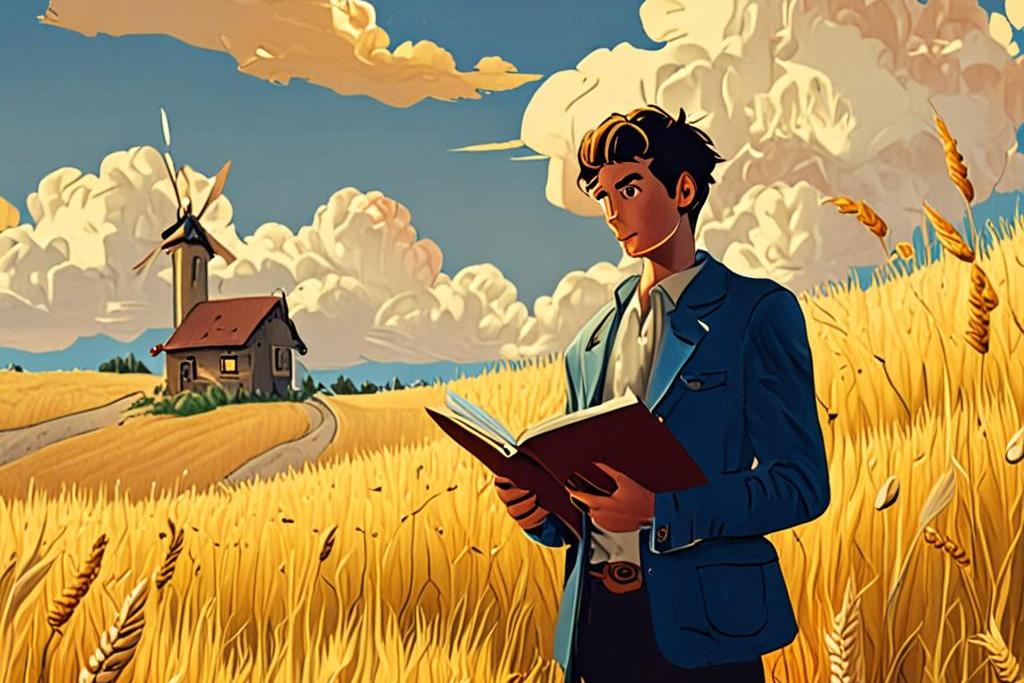大卫·西摩:老派的左派?还是披着羊皮的狼?
2024年8月5日 上午8:59
作者:布莱恩·伊斯顿
最近,行动党领袖大卫·西摩给自己贴了个标签——“老派的左翼人士”,这番言论一出,评论区瞬间炸锅了,堪比往平静的湖面扔了一颗深水炸弹,各种观点“duang duang duang”地冒了出来。
有些吃瓜群众表示一脸懵逼,以为西摩这是要“弃暗投明”,成为一名光荣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了。拜托,这脑回路也太清奇了吧!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在新西兰左翼阵营中崛起,那可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了,比咱们国家加入WTO晚了将近80年!早在1890年,新西兰左翼思想界的扛把子威廉·彭伯·里夫斯就写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涵盖了当时各种左翼思想,堪称左翼思想的“满汉全席”。然而,根据里夫斯的传记作者基思·辛克莱尔的说法,里夫斯对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毕竟在当时,马克思主义还只是左翼阵营中的“小透明”,远没有后来那么“火”。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不牛,人家可是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只是他的思想并没有成为新西兰左翼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西摩这番“老派的左翼人士”言论究竟是“真心话大冒险”,还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呢?让我们来品一品他的原话:“从很多方面来说,我是一个老派的左翼人士……我认为我们缴税是为了教育,这样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充分发挥他们的学术潜力。我认为我们现在做得并不好。” 好家伙,这不就是把1938年教育部长彼得·弗雷泽提出的弗雷泽-比比原则换了个马甲又拿出来说了一遍嘛!弗雷泽-比比原则的核心思想就是:“政府的目标,广义上来说,是让每个人,无论其学业能力高低,无论贫富,无论居住在农村还是城市,都作为公民有权接受与其最适合的类型的免费教育,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 [1]
其实,无论是西摩还是弗雷泽,他们都只是在重申一种在新西兰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理念——机会平等。想当年,我写《并非狭隘海洋》这本书的时候,就被一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为什么19世纪的欧洲人要千里迢迢移民到新西兰?要知道,当时去北美和澳大利亚可比来新西兰方便多了。
经过一番“抽丝剥茧”的研究,我发现,虽然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祖先渴望一个充满机会的“桃花源”,尤其是那些在英国工业化浪潮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梦想着在新西兰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开始,这些农场大多是自给自足的,与市场经济几乎没有瓜葛。但随着冷藏技术的出现,这些农场摇身一变,成了利润丰厚的商业企业,吸引了无数淘金者。
随着新西兰的城市化进程,机会平等仍然是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这在弗雷泽-比比原则和“新西兰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断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注意,“社会阶层”可不是马克思在“阶级斗争”中提出的政治阶层概念。)1959年,辛克莱尔曾豪言壮语地说:“新西兰不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然而,它一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更接近无阶级社会”。这话说得,就好像新西兰是什么“乌托邦”一样。
然而,现实却狠狠地打了辛克莱尔的脸。就在他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的朋友兼同事鲍勃·查普曼却在新西兰的城市中发现了新兴的阶级分化现象。这种分化就像病毒一样,不断蔓延,这意味着许多群体的机会正在逐渐减少。休·劳德和大卫·休斯的研究表明,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要想上大学,平均智商必须明显高于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这简直就是“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真实写照啊!当然,这项研究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的数据,我们不知道1990年后情况是变好了还是更糟了;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可能已经将最贫困的人群边缘化了。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因为出身不好,错过了本应接受的教育,这真是“输在了起跑线上”啊!更令人担忧的是,联合政府的教育政策可能会加剧阶级分化,因为它将使富人更容易为其子女购买优质教育资源,而穷人家的孩子只能“望尘莫及”。
毛利人的教育困境:被忽视的真相
以上讨论主要针对的是欧洲裔新西兰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巴克哈人”。而毛利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将毛利人和巴克哈人放在一起讨论,却忽视了毛利社会内部也存在着等级制度。这种将毛利人/巴克哈人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分界线的做法,掩盖了新西兰奥特阿罗瓦阶级问题的复杂性。随着阶级的演变,机会平等的目标逐渐消失。除了西摩,你还记得上一次有哪个政客谈论弗雷泽-比比原则是什么时候吗?[2]
因此,西摩提出教育机会问题,并希望引起更广泛的公众关注,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从根本上说,他的结论具有误导性。长期以来,新西兰一直有一种传统,那就是学校教育体系是提供机会的关键。这意味着它可以弥补家庭的不足。
然而,除了一个关键领域外,家庭如何失败和成功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如果我们给家庭施加经济压力,他们就更有可能失败。1990年理查森-希普利福利削减和新自由主义将税收从富人转向穷人的做法给家庭收入带来了额外压力,加剧了社会分化,减少了底层人民的机会。
西摩的“左派”面具下,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原则上,2018年的儿童减贫法案旨在解决这些压力,尽管阿德恩-希普金斯政府并没有全力以赴地实现其目标。通过降低目标,联合政府已经表明,它将更加不积极。孩子们将继续出现在教育体系中,无论投入多少钱,他们都无法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利用它。讽刺的是,西摩希望优先考虑加强国家而不是加强家庭。
如果西摩想把“左派”定义为支持促进所有人机会平等,那就这样吧。但在这种情况下,就他而言,右派是反对这一观点的。也许西摩真的是一个老派的左派。[3]
[1] 弗雷泽-比比原则实际上是由弗雷泽的部门主管克拉伦斯·比比起草的,并进行了性别修改,因为比比后来表示,他和弗雷泽都希望这样做,真是与时俱进啊!
[2] 当然,也有例外。一些新西兰经济学家,包括财政部的一些经济学家,讨论了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概念。这个复杂的概念与弗雷泽-比比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几乎没有对我们的公共政策产生任何影响。此外,还有一项为期15年的纵向研究“有能力的儿童”,也证明了家庭的重要性。
[3] 在其他领域,比如犯罪问题上,国家解决方案而不是支持私营部门也是政治权利的一个特征。这与托尼·布莱尔“对犯罪采取强硬态度;对犯罪根源采取强硬态度”的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
*布赖恩·伊斯顿是一位独立学者,身兼经济学家、社会统计学家、公共政策分析师和历史学家数职。他曾在1978年至2014年期间担任《倾听者》杂志的经济专栏作家。这是一篇最初发表在pundit.co.nz网站上的文章的转载。经许可在此发布。*